父母在家的24小时: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与守护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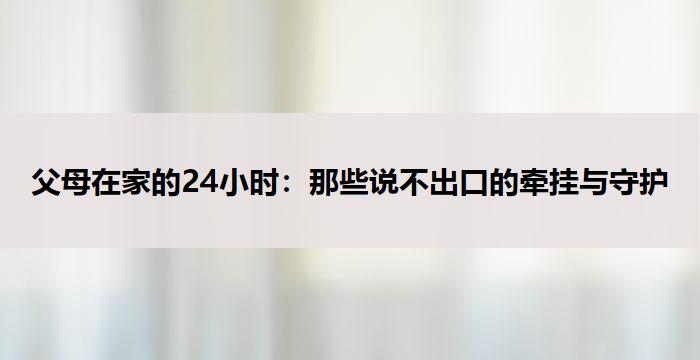
清晨五点,天还未亮,父亲已经轻手轻脚地起床。他习惯性地走到阳台上,望着远处泛白的天际,轻轻活动着有些僵硬的膝盖。母亲则在厨房里忙碌,熬了一锅小米粥,蒸了几个馒头,又特意煮了两个鸡蛋——即便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,她依然保持着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,仿佛下一秒,孩子们就会推门而入,喊着“妈,我饿了”。
七点,老两口坐在餐桌前,安静地吃着早餐。父亲偶尔会打开收音机,听一听早间新闻,母亲则时不时望向墙上的挂历——上面用红笔圈出的日子,是女儿上次回家的日期,已经过去两个月了。
上午:等待,成了生活的主题
吃完早饭,父亲戴上老花镜,坐在沙发上看报纸。其实报纸上的新闻他早已在手机上刷到过,但他还是喜欢翻动纸张的感觉,就像年轻时那样。母亲收拾完碗筷,拿起手机,犹豫了一会儿,还是点开了家庭群聊,往上翻了翻聊天记录,最后发了一句:“今天天气不错,记得多喝水。”
没有立刻收到回复,她也不急,只是把手机放在茶几上,转身去整理衣柜。她一件件抚摸着那些早已不再时髦的衣服,有些是女儿小时候穿过的,有些是儿子工作后给她买的。她轻轻叹了口气,又把它们整齐地叠好,放回原处。
中午:一个人的饭桌,两个人的牵挂
午饭很简单,一盘青菜,一碗汤,一小碟咸菜。母亲盛了两碗米饭,习惯性地把其中一碗多盛了一点——那是父亲爱吃的分量。父亲夹了一筷子菜,忽然说:“儿子昨天发朋友圈了,好像又加班。”母亲点点头,没说话,只是低头扒拉着碗里的饭。
午睡时,父亲躺在沙发上,电视里播放着午间新闻,声音调得很低。母亲坐在摇椅上,手里织着一件毛衣——其实家里没人穿手织的毛衣了,但她总觉得,织点什么,时间会过得快一些。
下午:沉默的陪伴
父亲醒来后,戴上帽子,慢慢踱步到小区楼下。他坐在长椅上,看着几个小孩追逐打闹,嘴角不自觉地扬起。母亲则去了菜市场,买了些新鲜的蔬菜,又特意绕到水果摊前,挑了女儿最爱吃的草莓。虽然知道孩子们近期不会回来,但她还是习惯性地备着,万一呢?
回到家,父亲正在摆弄那台老旧的收音机,滋滋的电流声里传出断断续续的戏曲声。母亲把草莓洗净,装在盘子里,放在茶几上。父亲看了一眼,没动,只是轻声说:“放着吧,等他们回来吃。”
夜晚:灯亮着,等一个不会响起的电话
晚饭后,母亲坐在沙发上,拿着手机,犹豫着要不要打个视频电话。父亲在一旁看报纸,偶尔抬头看一眼墙上的钟。九点,母亲终于拨通了儿子的电话,响了几声,没人接。她放下手机,笑了笑:“可能在忙吧。”
父亲没说话,只是起身去检查门窗是否关好,又顺手把客厅的灯调暗了一些——他们习惯了早睡,但卧室的灯,总会留一盏。
深夜:无声的守候
夜深了,整个城市渐渐安静下来。父亲躺在床上,听着母亲均匀的呼吸声,却迟迟没有睡着。他翻了个身,轻轻叹了口气。
窗外的月光洒进来,照在床头柜上的全家福上——那是几年前拍的,孩子们笑得灿烂,而他和母亲,眼里满是欣慰和满足。
父母的一天,就是这样平淡而沉默地度过。
他们没有说“我想你”,只是把牵挂藏在每一顿多做的饭菜里;
他们没有说“常回家看看”,只是把期待放在那盏永远亮着的夜灯里;
他们没有说“我老了”,只是在每一次电话挂断后,轻轻摩挲着手机屏幕。
他们的爱,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表达,而是日复一日的等待与守候。
如果可以,今天,就给他们打个电话吧。
哪怕只是听听他们的唠叨,哪怕只是说一句:“爸,妈,我挺好的。”
